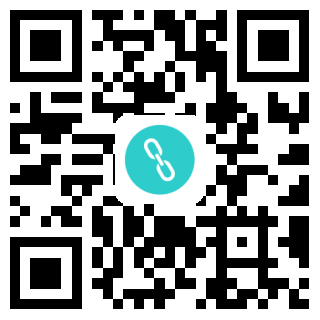倭寇的踪迹 万历野获编倭寇兴灭的细节
——《明史•列传九十三 朱纨》
从这段论述中,我们大致可以勾勒这样一个情状:闽浙势家也就是沈德符所言的“豪右”,他们对于朱纨损害他们走私利益的禁海政策颇有不满,自朱纨取得双屿大捷后,他们从心理抵触转化为以实际行动抵制朱纨对于倭寇的惩罚。从朱纨捕获的盗贼观之,其成员也不仅仅是日本人,也有中国人。而地方大族可以“挟制有司,以胁从被掳予轻比,重者引强盗拒捕律”,却也说明了一种更恶劣的情况:不仅仅有中国地方势力参与,甚而有官府势力混杂其中。
从豪右与倭寇的暧昧关系可以推断,朱纨认为倭寇的起因是由中方境内走私活动猖獗所引发。且以“去除中国盗难”而言他认为倭寇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恰恰是中国人。他深切明白“抗倭的关键是杜绝境内的走私商人的下海活动。”
回至疑问本身,我们便可以看到原先的两种解释其实并非真相,且不说日本人强夺豪右宝货是否真有,纵使为真,豪右迁怒于日本人也不会不助朝廷反助盗贼。因而,沈德符的真正含义正是通过“抚臣朱纨谈之详矣”明白地告诉我们:始(豪右)不过贸易牟利耳,继而(官府)强夺其(豪右)宝货,(官府)靳不与值,(豪右)以故积愤称兵。
(五)愚蠢的海防政策
在理清沈德符的逻辑思路后,他的说法是可取的。
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成果表示,嘉靖朝“倭患”实际上是由中国境内海商走私集团武装对抗明政府“禁海令”所引发的。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嘉靖“倭寇”实则是在中日走私贸易间渔利的中国海商及其追随者。 他们依托闽浙地方大族,进行走私贸易,而官府为了保护税收,强行扣留走私物资,自然也不会给予他们赔偿,这些以走私为生的海商气愤难平,与浪人勾结,转而为海盗,他们积愤的对象恰恰是明王朝的禁海令。
我们可以看一下时任浙江巡抚的胡宗宪编纂的《筹海图编》中关于中国贩于日本的货物:
丝: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。……若番舶不通,则无丝可织。每斤值银五十两,每百斤价银值二百两。
红线:常因匮乏,每百斤价银七十两。
水银:其价十倍中国。常因匮乏,每百斤价银三百两。
药材:甘草,每百斤二十金以为常。
从中我们已不难看出,如此丰厚的利润怎么能使中国商人因国家的海禁而放弃呢?相反,正是由于海禁才使得走私集团的货物显得奇货可居,至于铤而走险对抗官府也是利益驱使之使然。沈德符在此也认为海禁使“闽、广大家,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”。
关于嘉靖倭寇的复杂组成,当时人以及之后的部分学者有着清醒的认识。嘉靖时钱薇言:“今也,华人习知海外金宝之饶,夷亦知我海畔之人,奸阑出入,易与为市。……且如闽广群不逞之徒,明越诸得利之家,外交内,为彼耳目……是故处倭奴之策易,处奸党之策难。” 又有屠仲律言:“通番互市,夷十一,流人十二,宁绍人十五,漳泉福人十九,虽概称倭夷,实多编户之齐民也。”
与沈德符同时代的唐枢和谢杰的观点也可以作为旁证依理而循。唐枢作为时任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好友,在给他的信中写到:“嘉靖六七年后,守臣奉公严禁,商道不通,商人失其生理,于是转而为寇。” 谢杰在其《虔台倭纂》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倭寇的本质:“倭夷之蠢蠢者,其为中国患,皆潮人、漳人、宁绍人主也……寇与商同是人,市通则寇转为商,市禁则商转为寇。” 同时,他指出倭寇兴兵也绝非简单的 “靳不与值”所致,而是“病于海禁之过严” 。
根据中日学者关于倭寇的研究,越来越多的分析认为倭寇兴起的缘由是中国海商不满政府禁海,欲武力“要挟官府,开港通市”。山根幸夫在《明帝国与日本》中指出后期倭寇的主体是“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,不得不从事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”。他们的目的是“废止禁海令,追求贸易自由化”。 中国学者王守稼在《嘉靖时期的倭患》论述得更为彻底:明朝政府把王(汪)直集团视为“倭寇”,而王(汪)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“倭寇”的外衣。 他们其实是“假倭”,而“真倭”大多数是其雇佣的日本人,处于从属、辅助的地位。很明显,王(汪)直海盗集团的所为是对政府“假招安,真消灭”计策的报复,同时也是为了逃脱责任,而地方政府为了推卸实施这一计策失误的责任,也顺水推舟地以“倭人来犯”上报。可见,嘉靖“倭寇”是敌我共同编织借以掩盖双方责任的绝佳“借口”。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本站立场。奇迹在线网上有所的信息来源于互联网和奇迹在线无关,如有侵权请指出,我们立刻删除,本站不负任何法律责任。